
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速度已经慢下来了?《经济学人》9月13日发表名为“逆风回旋”的文章,称2008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回落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文章指出,在一些国家,要想进一步更好的发展,管理的质量和市场改革的引进需要更进一步被重视。一轮新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聚焦在了服务上,这会触发新一轮的全球化潮流。
“十年前开始,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速度追赶着发达经济体。这种速度甚至失之常理。”文章开头写道,随后举例中国。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中国的珠江三角洲更能清晰体现这种发展速度的了。生活水平甚至超过大多数最富有的欧洲国家的香港,就坐落在其河口位置。再往北走,你会经过集装箱港口深圳,在一片庞杂的房子和工厂的背景下,新的摩天大厦矗立其间。从1980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以来,其经济飞速增长,现在深圳市民的工资已经超过了一半的香港人,这大约接近欧洲中南部的水平。
“再向西北方向走点是广州,这是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在水稻田之间,横贯着新造的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广州的平均工资有香港的1/4,接近阿尔及利亚和哥斯达黎加。最后再往西,是一个分水岭,分支进入广西和云南,这是旅游大省,那里的工资大概是香港的1/10,接近安哥拉和刚果水平。”
《经济学人》9月13日发表名为“逆风回旋”的文章,称2008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回落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
文章指出,15年以来,这些内陆贫困地区的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蜂拥至开放广阔的“致富捞金地”。生活成本调整后,2000年到2009年,个人支出几乎翻了一番,而年均经济增长率在这期间高达7.6%,比发达国家高了4.5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迅速得在缩小。
“这种飞速发展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困状况。国际贫困标准是每天收入1.25美元以下,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高达30%,今年4月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0%以下。这种发展同时滋生了一些希望:如果发展中国家能保持每年比发达国家高4.5个百分点的增长势头,那么就像人均工资一样,其他的东西也会在30多年后与美国慢慢接轨,这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工业化曾开启了全球两极贫富分化,而当今的势头将又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并且是前所未有的。”
但文章立刻又指出:“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希望现在正在溜走。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4月发表的人均GDP数据(已考虑到新的生活成本的改变)分析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已经大幅减速。”
文章进一步解释道,2008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回落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新的世界银行的数据出来后,建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在2013年只比发达国家高2.6个百分点。如果不算中国,那么这个数据只有1.1个百分点。在这种速度下,如果还想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那么就不是一代人那么简单了,很可能需要的是一个世纪。如果囊括进中国,那么平均也需要超过50年的时间,而一旦除去中国,至少要115年才能赶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4的最新预测显示,未来的前景还要暗淡。除去中国,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只差了0.39个百分点。按这速率,赶超需要至少300年,这已经远远不在当今社会考虑的范围内了。”
《经济学人》认为,要回到10年以前的发展速度——看起来只要是世界想要就可以争取的经济恩惠,但是使那个阶段独树一帜的东西是无法轻易复制的。从现在开始,仅仅是跟上发达国家的脚步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将是一个挑战。发展所需的改革至今看起来仍不易达到,十几年来燃起的希望似乎在快速耗尽。
1997年,就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世界银行资深的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将贫富国家的两级收入差距描述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但是传统的经济学很难解释这种显著性。195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发表了一篇经济增长理论,他当时预测假以时日,贫穷的经济体应该会赶上发达经济体。
《经济学人》解释称,在索洛的模型中,经济不发达是因为其工人拥有的资本少,这种资本的缺少意味着高投资回报,因此资本会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从而使两者的生产力和工资往趋同的水平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发达一方仍会经济增长,这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索洛认为,发达国家长期的发展是由新技术推动的,那么同样地,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使用新技术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从发达国家发展的失误中获得前车之鉴,从而直接跃进。
历史上,这种模型非常适用于后富国家。在开拓性的工业革命促进下,19世纪英国的人均GDP远超其他国家。到1870年,英国已经比美国高产30%,比德国高70%。但是这种优势在对手的技术也相继提高后渐渐地消失了,到20世纪,美国已超过了英国,二战后不久,大多数西欧国家也都赶了上来。
“但是欧洲在适宜的气候后创造的东西包括它开发的殖民地都是无法照搬给其他地方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这是很少见的,持续保持这种速度,更是少见。从4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无论哪个时期都只有少于1/3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文章称。
文章举例称,有些亚洲经济体是例外。日本在20世纪初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和少数几个城市规模的经济体,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是富有的。但是非洲和中东在60-70年代的发展前景在逐渐消失。这种沉闷让悲观的科学家感到相当的抑郁。
此外,“东欧和东亚经济体仍差距显著,尽管对很多东欧国家来说,很大一部分的增长仅仅只是苏联解体以来经济收缩的恢复。1998年,波兰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8%,中国是7%;到2013年,这个数据分别上升到了44%和22%。其他国家的增长就更少了,巴西的人均收入1998年是美国的25%,到2013年只增长了3个百分点;对贫困国家来说,哪怕是很高的发展速度,但追赶上来仍不多,诶塞俄比亚的人均GDP只从美国的1.3%增长到2.5%。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更被甩在后头。”
《经济学人》指出,在一些国家,要想进一步更好的发展,管理的质量和市场改革的引进需要更进一步被重视。
这其中之一就是良性的宏观经济环境,在21世纪,利率低,资本流动自由;另一个是大宗商品的物价飞涨,很多新兴经济体对自然资源的出口依赖性强,但是与大宗商品物价飞涨无关的全球贸易是最大的推动力。从1980年到1993年,全球贸易平均每年增长4.7%,或在3%多一点。1994年到2007年间,贸易增长速率几乎是世界经济增长速率的两倍,商品出口飙升到全球GDP的1/4。
“在这其中占最大份额的雄狮是中国。在这期间,中国的贸易不仅对其本国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对全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和凯斯勒(Martin Kessler)把这段期间称作‘超全球化’。此前唯一一个达到这种影响力的经济体只有19世纪的英国。”
有两个大的因素推动了这种转变。文章认为,一是1995年世贸组织的建立,贸易自由达到了极点,而中国在2001年加入。二是科技发展为供应链的更长、更复杂性提供可能。到90年代,集装箱运输使货物在全世界内比以往更方便、更低廉地得以运送,并且需要增加运输力的港口可以很快很轻易地建造。沟通也更加方便,以电脑为基础的设计技术的发展,使精细的零件细节得以很轻松地两地传送。国际贸易越来越方便,成本越来越低廉,这使得原本因国家地区而地域隔离的供应链得以扩展到全球规模。这些加速了发展中国家赶超的速度。当年日本和韩国需要靠建设工业和提高技术能力的地方,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只需稍微多提供一点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加强一点对工厂进出产品的管理。
“完全靠制造业推动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担忧。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丹尼•洛迪克(Dani Rodrik)指出,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工业就业的比例在下降;而今,比起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制造业上雇佣人越来越少。而通常,一个经济体内,工业享有高峰就业比例,现在其收入水平几乎下降了一半。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通常能适应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仅仅靠发展制造业就可以消除的与发达国家富裕水平的差距,这已经在下降了。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巅峰及高速发展阶段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现在可以看到,它们的追赶停在了令人失望的低收入水平上。”
文章指出,最后一波“趋同”可能已经接近于耗竭了潜力,这种潜力来自改革意识和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根据一份国际增长中心(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的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有着跌破底价的劳动力成本,印度在制造业的劳动强度也已经下降。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持续的对劳动法的严格约束,它打破了低工资的竞争优势。在最近的“趋同潮”中受益最少的是那些不太容易的经济体,它们往往基础设施是最不发达的,政府是最腐败的,基本安全是持续令人担忧的。
“但是,对于那些仍想抓住机会的人来说,前进的道路还是有的。一轮新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聚焦在了服务上,这会触发新一轮的全球化潮流。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就业率的大幅下降,发展越来越意味着从农业转向城市服务行业。扩大易跨境交易的服务范围将能使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参与到生产率和工资都更高层面的行业上来。但服务业仍高度受限。最富裕国家俱乐部一直在努力协商更新在1995达成的服务贸易协议。但进展仍然很小。”
文章最后说道,在世纪的转折中,出现了大宗商品热和超全球化,而现在没有什么努力能带来像这样宏大的收获。在这种刺激的缺乏下,历史表明,消除差距将会是一场漫长又艰难的折磨,它依靠制度的慢慢改善和劳工技术水平的慢慢提高。过去的15年改变了关于究竟什么是可能的看法,但它也给了人们“广泛的趋同是事物发展的自然方式”的错觉。它看起来正在提醒人们,消除差距是很难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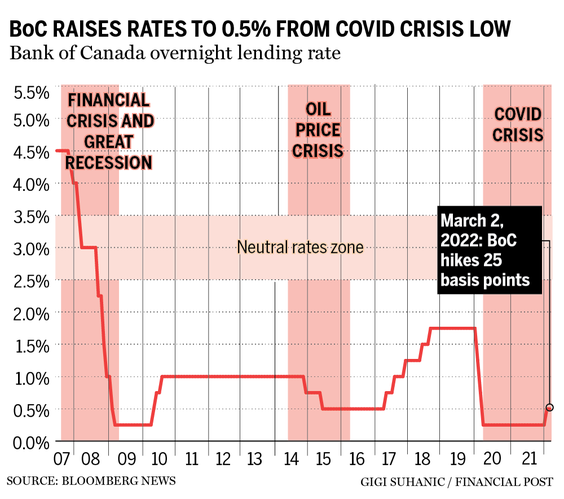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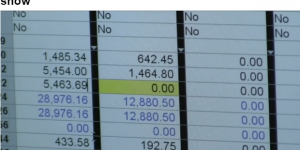 加拿大税务局正在加速收债 发出两个重要提醒
加拿大税务局正在加速收债 发出两个重要提醒

 加拿大政府疫情期间到底有多豪?
加拿大政府疫情期间到底有多豪?

 在加拿大怎样注册公司?
在加拿大怎样注册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