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与一些欧美政策制定者同桌吃饭,有美酒佳肴相伴,宾客们相谈甚欢。聊着聊着,话题转向了希腊。“你知道什么才能解决那儿的问题吗?”一位经济学家开怀大笑道:“度假营!”
“度假营?”我困惑地问道。这位经济学家用餐巾作演示,提出了这个想法。他的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需要动用些德国纳税人的钱,建造或翻新希腊那些美不胜收的度假胜地,只雇佣当地劳动者。然后再指定第二笔纳税人资金,用于给德国退休人士发放度假代金券,让他们能够享有一个费用全包的假期,但这些代金券只能“花在”希腊那些度假胜地上。
我的这位同席伙伴认为,这个协议将为希腊的经济活力带来亟需的提振,还能迫使德国将一部分盈余现金在境外花掉,从而有助于扭转欧洲内部的经常账户失衡。但他认为这个计划最棒的地方在于,至少与另一个选项——将德国纳税人的钱填到陷入困境的欧元区银行的黑洞里——相比,它为德国纳税人提供了一些他们喜欢,从而有可能在政治上支持的东西。这位经济学家在全桌人的爆笑声中总结道,“如此一来,德国退休人士开心了,希腊服务员也开心了”,这个计划堪称“完美的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版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这无疑是个有趣的想法。每当我在饭桌上或是会场讲台上讲起这个段子,总是能活跃气氛。比如本月早些时候,我在阿斯彭理念节(Aspen Ideas festival)上主持一场关于希腊的(激烈)辩论时,随口提到这个凯恩斯主义(Keynesian)的度假营计划,引发了现场亟需的哄堂大笑。
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类学家所指出,笑话从来不是无关紧要或疯狂的东西。笑话之所以有感染力、并且好笑,是因为它们颠覆了正常的社会与认知秩序,揭示了我们通常宁愿视而不见的矛盾。因此随着希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探究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个“地中海俱乐部”版解决方案听上去那么好笑?关于欧洲领导人现在不愿谈论的那些话题,它揭示了什么?
在我看来,这个笑话揭示了两点。第一,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个根本致命缺陷是,选民很难感觉到自己受益于政府四处挥洒的大笔欧元。如果纳税人的钱被用来建造桥梁或资助学校,起码这些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让他们受益的。选民甚至可能还会感激。但把钱投入银行,这就没人能看到了,量化宽松是一种空洞无形的东西。因此,这个用国家资金为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乐趣的想法听起来就像个笑话。现如今,幸福快乐被默认为只能从私营部门找到,与欧盟官员无关。难怪选民们不开心。
关于为什么地中海俱乐部方案如此有感染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似乎很难想象欧元区各国政府会为集体利益亲密无间地合作。理论上,单一货币体系想实现良好运行效果,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欧洲内部能够拧成一股绳,像一个整体经济区那样运行,每个区域都能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让劳动力和资本往需要的地方流动,就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劳动分工的概念所描述的那样。
别的地方是有这样的例子的。比如美国佛罗里达州,近几十年来,这个州将自己打造成了所谓的“雪鸟”,即美国北方居民的首选目的地,从而实现了经济繁荣。每年,尤其到了冬季,前往佛罗里达州避寒的“雪鸟”数以百万计,有些人在那儿买了房,或在那儿退休养老。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这么做,是因为佛罗里达的物价相对便宜,迁入门槛不高,而且在语言、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与美国北方相同。
欧洲也有“雪鸟”,看看地中海海滩上坐着的那些苍白的英国人、德国人和瑞典人就知道了。但欧洲的“雪鸟”现象没有应有的那样盛行,因为文化、语言和法律上的差异持续存在。事实上,2010年代伊始,德国前往希腊的游客人数急剧下降。虽然去年游客数量有所回升,但眼下的危机似乎再一次把游客们吓跑了。希腊和德国的有钱人反倒是纷纷涌向迈阿密等地购买房产。
这对希腊而言是痛苦的,因为旅游业占了希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五分之一。这也与经济意义上让欧元区行得通所必须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所以才有了那位经济学家关于地中海俱乐部版马歇尔计划的笑话。
他的玩笑话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吗?几乎肯定不会。如果有人建议强行将德国退休人士送到希腊度假,这个人会被抗议声淹没的。但欧洲的情况越糟糕,我们就会越需要疯狂的想法,甚至是笑话。而这不止因为我们需要笑一笑,还因为笑话揭示了政客们没有在谈论的事,即,如果欧元区计划想要有成功的那一天,欧洲必须出现认知和文化上的飞跃。不管德国退休人士去不去地中海海滩度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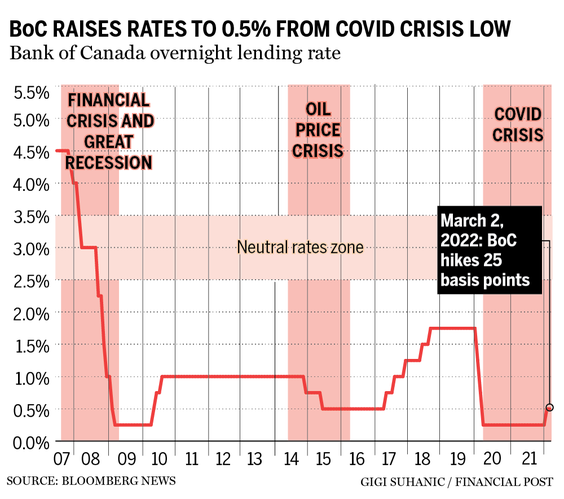



 在加拿大怎样注册公司?
在加拿大怎样注册公司? 新移民加拿大买房九步骤
新移民加拿大买房九步骤
 华人尤其需要注意这些细节,2018美国退休福利新变化!
华人尤其需要注意这些细节,2018美国退休福利新变化!